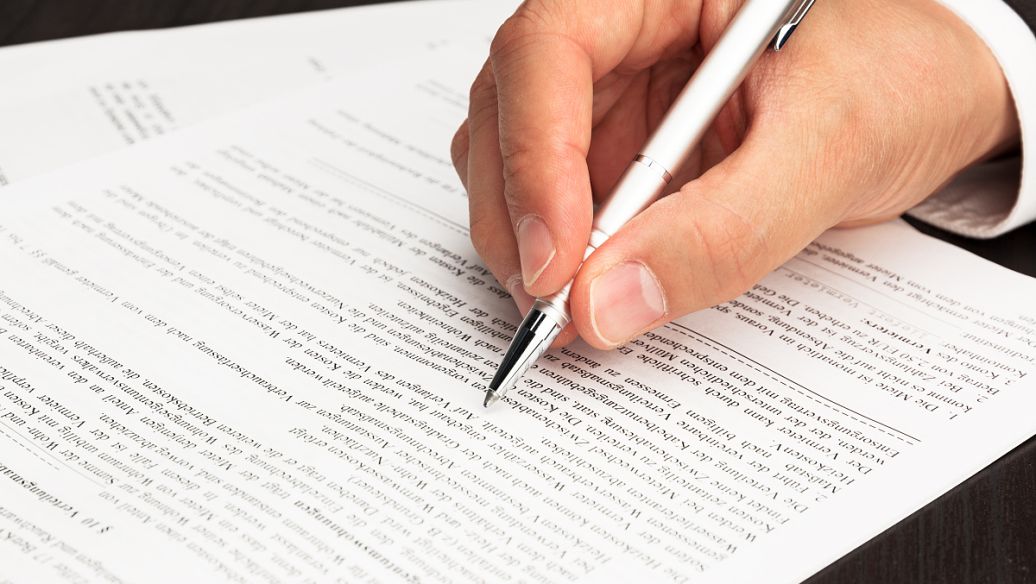原谅你逃避过去,但是,至少不要逃避现在和明天。因为我们总是在注意错过太多,却不注意自己拥有多少。而且,在旅途的过程中,我不认为依赖一个人有什么不对,在你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人与人之间总是紧密相连的,只要你伸出手我们就在你的身边。然而不请自来又不告而别的事物,即使彼此之交汇过一次,即使微弱得不会被人注意,那也是能够支撑心灵的,重要的邂逅。有些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也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吧,但是我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声音,你的眼眸,与你看到过的所有的景色,以及,与你一起度过的那个耀眼的夏天。毕竟谁也没有办法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笔勾销,况且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都是用朴素的童真与未经人事的洁白交换长大的勇气。就算活着感受到痛苦,也要重视起生存下去的重量。毕竟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想生存。。。但是我们怎会有不同的想法?一知半解的知性,会为细小的事产生误会,继而谎话成真,产生歧视,最后无法互相理解。。。只是,我们没发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昭示出来,就算你不被认同,难道就无法存在了么?或许你能轻松说出我在努力这种话,可这就是还在放纵自己的证据,这样根本不能算是在努力。可况对自己撒下的细小谎言,既无法称赞也无法责备。因为重要,因为不想失去。隐藏着,伪装着。正因如此才一定会失去。于是,就会悲叹起得失,觉得还是不要得到会更好,如果离手之时会后悔到死的话,还是放弃会更好。毕竟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外在或内在,而是看他的行为。或许没人能让时光倒流,然后重新再出发,但所有人都可以在今天启程,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结局。也许人的一生如负重远行,干脆丢掉行李会比较轻松,但无论怎样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行李的话,走起路来会多么无趣。
作文吧 关注:130,939贴子:981,450
原谅你逃避过去,但是,至少不要逃避现在和明天。因为我们总是在注意错过太多,却不注意自己拥有多少。而且,在旅途的过程中,我不认为依赖一个人有什么不对,在你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人与人之间总是紧密相连的,只要你伸出手我们就在你的身边。然而不请自来又不告而别的事物,即使彼此之交汇过一次,即使微弱得不会被人注意,那也是能够支撑心灵的,重要的邂逅。有些事情是要说出来的,不要等着对方去领悟,因为对方不是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等到最后只能是伤心和失望,尤其是感情。也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吧,但是我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声音,你的眼眸,与你看到过的所有的景色,以及,与你一起度过的那个耀眼的夏天。毕竟谁也没有办法把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笔勾销,况且成长是一笔交易,我们都是用朴素的童真与未经人事的洁白交换长大的勇气。就算活着感受到痛苦,也要重视起生存下去的重量。毕竟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想生存。。。但是我们怎会有不同的想法?一知半解的知性,会为细小的事产生误会,继而谎话成真,产生歧视,最后无法互相理解。。。只是,我们没发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昭示出来,就算你不被认同,难道就无法存在了么?或许你能轻松说出我在努力这种话,可这就是还在放纵自己的证据,这样根本不能算是在努力。可况对自己撒下的细小谎言,既无法称赞也无法责备。因为重要,因为不想失去。隐藏着,伪装着。正因如此才一定会失去。于是,就会悲叹起得失,觉得还是不要得到会更好,如果离手之时会后悔到死的话,还是放弃会更好。毕竟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外在或内在,而是看他的行为。或许没人能让时光倒流,然后重新再出发,但所有人都可以在今天启程,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结局。也许人的一生如负重远行,干脆丢掉行李会比较轻松,但无论怎样也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行李的话,走起路来会多么无趣。
人们认为,最伤心的回忆来自痛苦的经历,其实最伤心的莫过于,那些无法再现的辛福的经历。假如有个人愿在自己身边,就算没有任何语言只是在身边,我也觉得是一种幸福,即使失去了一切,只要停下脚步看一下四周,一定会有某个人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请别伤心、不要绝望,无论如何也请别忘记,自己绝不是孤单一人的。因为即使相处的时间不多,但所谓的友情是不在乎相处的时间长短的。其实朋友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未必要什么天长地久,也未必时时见面联系。在一些时候,可以彼此温暖,彼此慰藉,彼此鼓舞,那就足够了。而且我觉得不可靠和脆弱没什么不好,正因为如此,心灵相通的时候才感到无比的温暖,如果友情是那种生硬的像铁一样的东西,是不会感到温暖的。有时候我们只能躲在角落里,显示永远是那么残酷。明明我也想要一个朋友,但是始终会被遗弃。或许就算有一天,离别的时刻来临,但那也不一定意味着永别吧。而最近感到困扰的是,连小小的离别都会觉得有点寂寞。况且强忍着泪水却笑着说离别再见是如此伤感。而我们仰望着同一片天空却看着不同的地方。在我看来年轻的好处,是可以在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之前,做率性的事。荒唐也好,可笑也好,那都是无悔的青春。而有形的东西迟早会凋零,但只有回忆是不会凋零的。因为回忆这种东西,越是美好,越是伤人。曾经笑得有多灿烂,如今就会有多沮丧。在某个我们彼此都希冀的地方,若我们再次遇见,在我们心灵的归处,已各自生活在各个领域的大家又能否像以往般的要好?而且如果把童年再放映一遍,我们一定会先大笑,然后放声痛哭,最后挂着泪,微笑着睡去。毕竟我们会慢慢长大成人,随着季节的不断变换 路边的鲜花也在不断变化。那年,未来遥远得没有形状,我们单纯得没有烦恼。而在我看来,所谓长大成人,就是不断聚了散,散了又聚。为了让彼此不会受伤害而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而坚强,不是面对悲伤不流一滴眼泪,而是擦干眼泪后微笑着面对以后的生活。而且与其伤害别人,我宁愿被伤害。因为温柔的人光是这样就很幸福了。语言是把利刃,使用不当便会成为可怕的凶器,因为一句话可能会失去一生的挚友。一次擦肩而过,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所以愿这双闭上的眼睛再次睁开时,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而天空是连着的,如果我们也能各自发光的话,无论距离有多远,都能看到彼此努力的身影。
她说
冬天就快来了。南方的冬天总是温柔的,地面没有铺上属于它的服饰,而是依旧保留随处可见的绿,那是南方的冬所喜欢的颜色,谁也带不走。
柴火烧出的木屑味,合着一种焦制的独特气息,在这个小院里环绕着。浓浓的灰烟飘向街道,偶尔听的见两声咳嗽声,其他的声音都掩埋在巨大的汽车尾声和笛鸣里。
那是一个有着太多回忆和曾经的巷子,两排长长的木椅早已在岁月的风雨中变得暗沉、潮湿。可是,这里的老人却最爱这个地方,最爱这一处带着木头腐败的气味,坐在那排摇摇晃晃的长椅上,看着外面不断来往的人群和车流。
奶奶总是喜欢去楼下,擦拭着早已平滑干净的木椅,然后缓缓坐下,和这里的老人聊着。她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老厂,这里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和人世变迁;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呆了快三十年,看着这座老厂房由崭新变得老久,看着这里的老人一年年的减少;她说,她舍不得这栋老楼和家,再雄伟再美的高楼大厦都没有这里留下的气息让自己留念;她说,她喜欢这个围在城里的小火炉,每年都能飘出属于冬天独有的柴火味。她还想说很多很多,可是,在这二十年的时光流逝中,我已经记不清那曾经蠕动的嘴里究竟还在说什么。
在那个工人面临下岗的时代,很多家庭的年轻人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人家里,然后外出打工。那些灰色的建筑,几乎剥落殆尽的暗黄墙漆,一道道竖起的围墙,就成了院里不断长大的孩子和老人的回忆。
那时候,公交车还是统一贴着绿色胶纸的样式,在这个小城市里,汽车还没有占满整个街道。奶奶喜欢牵着我们的手,在周末的时候搭着公交车去周边的小镇。公交摇摇晃晃的走过很多地方,那是留在童年记忆里还有的遍地的绿和黄。每当日落时,车子在三桥上驶过,奶奶就会拍拍我们的肩头让我们望向车窗外,模模糊糊的记忆中,那些橘红的太阳在没有高大建筑物的阻挡下,慢慢的消失在这个丘陵环抱的小城中。她说:“太阳回家了,我们也要到达终点站了。”每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央求着奶奶下次还要带我们去玩儿,她会笑着抚摸我们的头,亲吻我们的面颊,说好。那从来不是一个无聊的年代,那些每时每刻都黏在亲人怀里的时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清晰的记得一个又一个瞬间。那也不是一个贫乏的时代,每一个孩子都能提着手中烧的火红的炉子,在小园里跑着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声影,永远刻在这个小院的印记中。
三个月前,我回到家中,看着无聊刷着手机屏幕的奶奶,对着那只会说话的汤姆猫笑的像个小孩子。我笑话她变得越来越前沿,都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差不多,她说我们太久没陪她了,她也没事干。不知怎么,当时的心中很难受。下午,我就陪着奶奶再一次乘公交车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公园、花园市场、新开发的小镇。一路上,奶奶不断指着那些一年比一年高耸的建筑。她说,这里曾经是一大片农田。可是,农田已经变成了购物中心。她说,这里曾经是她小时候住的院子。可是,院子变成了老年活动场所。她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天然的小湖泊。可是,小湖泊填平了,修了工厂。她说,这里是她带着很小的我们玩过的草坪。可是,草坪已经变成了绿化带,再也没有从前的样子。这一次,她每一句话我都认真的听了,也看着她不同于以前的模样,长出的长长的皱纹,从眼前到达了耳边;染着深红色的头发,也能一眼看见的花白的发根;那双温暖的手再一次抚摸我的面颊时,有些坚硬的茧子,磨的微疼。夕阳落下时,因为路线的原因我们没有经过三桥,她说拍一张照片吧,她要洗出来存在相册里。当快门按响的时候,那位帮我们拍照的陌生人笑着说背景很漂亮,橘红的太阳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只是曾经留在杯子上一样的两人已经变换了身高,留在岁月变迁的历史里。夜晚,奶奶吃了很多东西,似乎在好心情的影响下,每一个人都会年轻很多。她和老爷子唠叨今天的事,老爷子依旧和奶奶拌嘴。灯光下,两个人的画面,就像电视里的场景一样,我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最珍惜的人,最珍惜的时光。
清晨的光照射进屋子里,我又闻见那股浓浓的木屑味,我出了房间门,看着楼下燃起的铁皮炉。奶奶还是坐在那排木椅上,穿着厚重的袄子,和那些同年代的老人聊着天,那些从楼下传来的笑声,带着老年人的口气。我又靠在窗前,看着这个有着绿叶的冬,它爱这个小城的故事,而我,爱这个小巷里的生活。
冬天就快来了。南方的冬天总是温柔的,地面没有铺上属于它的服饰,而是依旧保留随处可见的绿,那是南方的冬所喜欢的颜色,谁也带不走。
柴火烧出的木屑味,合着一种焦制的独特气息,在这个小院里环绕着。浓浓的灰烟飘向街道,偶尔听的见两声咳嗽声,其他的声音都掩埋在巨大的汽车尾声和笛鸣里。
那是一个有着太多回忆和曾经的巷子,两排长长的木椅早已在岁月的风雨中变得暗沉、潮湿。可是,这里的老人却最爱这个地方,最爱这一处带着木头腐败的气味,坐在那排摇摇晃晃的长椅上,看着外面不断来往的人群和车流。
奶奶总是喜欢去楼下,擦拭着早已平滑干净的木椅,然后缓缓坐下,和这里的老人聊着。她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老厂,这里见证了太多的变化和人世变迁;她说,她已经在这里呆了快三十年,看着这座老厂房由崭新变得老久,看着这里的老人一年年的减少;她说,她舍不得这栋老楼和家,再雄伟再美的高楼大厦都没有这里留下的气息让自己留念;她说,她喜欢这个围在城里的小火炉,每年都能飘出属于冬天独有的柴火味。她还想说很多很多,可是,在这二十年的时光流逝中,我已经记不清那曾经蠕动的嘴里究竟还在说什么。
在那个工人面临下岗的时代,很多家庭的年轻人不得不将孩子留在老人家里,然后外出打工。那些灰色的建筑,几乎剥落殆尽的暗黄墙漆,一道道竖起的围墙,就成了院里不断长大的孩子和老人的回忆。
那时候,公交车还是统一贴着绿色胶纸的样式,在这个小城市里,汽车还没有占满整个街道。奶奶喜欢牵着我们的手,在周末的时候搭着公交车去周边的小镇。公交摇摇晃晃的走过很多地方,那是留在童年记忆里还有的遍地的绿和黄。每当日落时,车子在三桥上驶过,奶奶就会拍拍我们的肩头让我们望向车窗外,模模糊糊的记忆中,那些橘红的太阳在没有高大建筑物的阻挡下,慢慢的消失在这个丘陵环抱的小城中。她说:“太阳回家了,我们也要到达终点站了。”每当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央求着奶奶下次还要带我们去玩儿,她会笑着抚摸我们的头,亲吻我们的面颊,说好。那从来不是一个无聊的年代,那些每时每刻都黏在亲人怀里的时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清晰的记得一个又一个瞬间。那也不是一个贫乏的时代,每一个孩子都能提着手中烧的火红的炉子,在小园里跑着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声影,永远刻在这个小院的印记中。
三个月前,我回到家中,看着无聊刷着手机屏幕的奶奶,对着那只会说话的汤姆猫笑的像个小孩子。我笑话她变得越来越前沿,都和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差不多,她说我们太久没陪她了,她也没事干。不知怎么,当时的心中很难受。下午,我就陪着奶奶再一次乘公交车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公园、花园市场、新开发的小镇。一路上,奶奶不断指着那些一年比一年高耸的建筑。她说,这里曾经是一大片农田。可是,农田已经变成了购物中心。她说,这里曾经是她小时候住的院子。可是,院子变成了老年活动场所。她说,这里曾经有一个天然的小湖泊。可是,小湖泊填平了,修了工厂。她说,这里是她带着很小的我们玩过的草坪。可是,草坪已经变成了绿化带,再也没有从前的样子。这一次,她每一句话我都认真的听了,也看着她不同于以前的模样,长出的长长的皱纹,从眼前到达了耳边;染着深红色的头发,也能一眼看见的花白的发根;那双温暖的手再一次抚摸我的面颊时,有些坚硬的茧子,磨的微疼。夕阳落下时,因为路线的原因我们没有经过三桥,她说拍一张照片吧,她要洗出来存在相册里。当快门按响的时候,那位帮我们拍照的陌生人笑着说背景很漂亮,橘红的太阳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只是曾经留在杯子上一样的两人已经变换了身高,留在岁月变迁的历史里。夜晚,奶奶吃了很多东西,似乎在好心情的影响下,每一个人都会年轻很多。她和老爷子唠叨今天的事,老爷子依旧和奶奶拌嘴。灯光下,两个人的画面,就像电视里的场景一样,我坐在那里,看着这些最珍惜的人,最珍惜的时光。
清晨的光照射进屋子里,我又闻见那股浓浓的木屑味,我出了房间门,看着楼下燃起的铁皮炉。奶奶还是坐在那排木椅上,穿着厚重的袄子,和那些同年代的老人聊着天,那些从楼下传来的笑声,带着老年人的口气。我又靠在窗前,看着这个有着绿叶的冬,它爱这个小城的故事,而我,爱这个小巷里的生活。
想去看风景,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
有人喜欢江南水乡的温婉,细雨打湿的油纸伞,湖水从青石桥下流过,那里就像画中的情人,懵懵懂懂,隔着一张薄纱,隐隐的看见一个模糊美妙的倩姿,又能感受到一股清雅的淡香飘散在心间。有人喜欢北方腾格里的粗狂,驼峰背着落阳,铃铛的声音飘散在广阔的土地,豪迈的歌声夹杂着淡淡的忧思,炊烟升起的时候,传出木屑的焦味,还有夜里带着无限寂寥的风沙。七月的初夏,南方的雨并不温柔,淅淅沥沥是苏杭文客描绘的景,在巴蜀的雨总是在述说着它的到来。
峨眉,似乎在嘴里念出总有着一种曼妙娟秀的感觉。不同于唐古拉和青城的陡峭,也没有华山凌云般的雄伟,留在人们的映像中,它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清秀文雅。
六月末,初夏就像一个青涩的孩子,在奔跑的同时,手里拿着一支翠绿的柳条,带着股淡淡的香还有它独有的声音。在山里的时候,这种独特的美和宁静似乎被无限放大,就连平时照射在脸上的碎阳都像是被放进相册里的泛黄图片,这也似乎成了爱山一族的爱丽丝梦境。
我曾两次去往这座被无数次写画的山,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游记与碑文也在向岁月展现它的悠远。每当大巴驶进山里,我都希冀着这些轰鸣声不要打扰了山的深沉。摸着这些湿滑的岩石,凉凉的,却又十分亲切。
我们在凌晨五点四十从山脚出发,夜里下起了雨,一直到凌晨才有减弱的趋势。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浅浅的水洼还有雨滴滴落下来打出的晕圈。偶尔有几辆闪着微弱灯光的载物车从身边经过,轰轰的开向山脚的旅店,微弱的蝉鸣和山里的静谧让我还能听清自己的呼吸声。日出总要早一些,快要六点时,微微的亮开始布满这座沉睡的山。我们不断加快着步子,看着每隔不远就有的用白色大理石修建的宛如英式教堂长廊的石巷。石廊上的漆已经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锈迹斑斑,深褐色的砖瓦上铺满了青苔,偶尔还能看见一两个燕子窝搭建在上面。
趁着天亮,我才看清悬崖下的流水,山脚的地势平坦,从山上留下的泉水虽然势力不大,但依旧能清楚的听见它在山谷中的冲撞声。从上往下看去,细细的流水像是一条银白色的长带,在微亮的谷中,还闪着一点点水光。山的对面,尚是翠嫩的新枝斜挂在悬崖上,那些粗壮的根脉一直衍生到山顶,像是网状一般,牢牢地攀附在山面。肥硕的叶子幽绿幽绿的,将新生的枝干掩护起来,悬空的漂浮在空中,微风吹过的时候,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就像是在和山谷打着招呼,向这个刚刚到来的初夏说着悄悄话。
我们乘车到的山顶,雷洞坪到金顶的这一段路程,如果选择乘坐观光缆车上去,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运气好,还可以享受一次腾云驾雾的感觉。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时间还很早,空气中还有微微的雾气,却并不感觉冷。站在一处小斜坡,靠在石栏上向远方望去,山重着山, 隐隐约约的,望不到尽头。云成朵状分布,小块小块的,笼罩着山峰。这些青草都还稚嫩,刚开的雏菊还有偶尔飞过的柳絮,映着不远处的佛塔,母亲裹着头巾从声旁经过,表妹一如既往的拿着相机拍摄,这种安宁的美,一直都寄托着我对山的感恩。
华藏寺上烟雾缭绕,香客来来往往,从阶梯第一层开始揖拜,长长的檀香举在头顶,虔诚的向佛像走去。常青树和柏松栽种在阶梯两旁,用大理石做成的白象,以及刻着铭文的青铜鼎,还有抬头就能望见得金佛。我转身寻找着母亲的身影,她佝偻着身子,将沉香插进鼎中,双手合十,嘴里低低的念叨着,最后深深地一拜,就朝我们的位置走来。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当你虔诚揖拜时,佛就在你的心里。’
当经过大雄宝殿时,正好僧人敲响了铜钟,沉沉的回声,还伴着僧人的吟诵声。我缓缓侧过身,看着这巍峨的建筑物,释迦牟尼佛盘坐着,低垂着眼眉,面相慈和。香烟围绕着整个大殿,蓝天似乎只是做了背景,在这没有任何污染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闲的格外真实。佛语的传唱,没了敦煌的悠远与留恋,却有着峨眉的深沉和安宁。
在山顶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下了山。年轻人总是活跃一点,互相争着走在前面,偶尔停下来取笑着杵着竹竿、颤颤巍巍行走的母亲,在一顿谩骂中,继续嬉笑着往下跑。
山路并不是许多人口中的无趣,当你用心去看时,才会发现它们的美。这些千奇百怪的树干和树枝,在没有人工的栽培下,有的笔直,有的却纵横交错。树枝交叉着树枝,像是武器交锋,扎进了山缝里,青藤将它们缠起来,把阳光分成碎块,洒在黄岩上,蜂鸟和猴儿喜欢停在上面,享受自然给的沐浴。这些绿的植物中偶尔也会点缀着其他颜色的生物,黄的、白的、紫的,木兰的香味淡淡的,当你停留久时,这股幽香就会变得浓郁。山崖下是望不清的薄雾,有游人在下面吆喝着,有时还会传出猴子的啼叫声。大自然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那些无法想象的奇观,山崖被劈成两半,成六十度对角折叠起来,白云和雾气围绕着这座悬崖,只有树的梢头暴露在人们的视野里。
有人喜欢江南水乡的温婉,细雨打湿的油纸伞,湖水从青石桥下流过,那里就像画中的情人,懵懵懂懂,隔着一张薄纱,隐隐的看见一个模糊美妙的倩姿,又能感受到一股清雅的淡香飘散在心间。有人喜欢北方腾格里的粗狂,驼峰背着落阳,铃铛的声音飘散在广阔的土地,豪迈的歌声夹杂着淡淡的忧思,炊烟升起的时候,传出木屑的焦味,还有夜里带着无限寂寥的风沙。七月的初夏,南方的雨并不温柔,淅淅沥沥是苏杭文客描绘的景,在巴蜀的雨总是在述说着它的到来。
峨眉,似乎在嘴里念出总有着一种曼妙娟秀的感觉。不同于唐古拉和青城的陡峭,也没有华山凌云般的雄伟,留在人们的映像中,它就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清秀文雅。
六月末,初夏就像一个青涩的孩子,在奔跑的同时,手里拿着一支翠绿的柳条,带着股淡淡的香还有它独有的声音。在山里的时候,这种独特的美和宁静似乎被无限放大,就连平时照射在脸上的碎阳都像是被放进相册里的泛黄图片,这也似乎成了爱山一族的爱丽丝梦境。
我曾两次去往这座被无数次写画的山,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游记与碑文也在向岁月展现它的悠远。每当大巴驶进山里,我都希冀着这些轰鸣声不要打扰了山的深沉。摸着这些湿滑的岩石,凉凉的,却又十分亲切。
我们在凌晨五点四十从山脚出发,夜里下起了雨,一直到凌晨才有减弱的趋势。青石板铺成的路面上,浅浅的水洼还有雨滴滴落下来打出的晕圈。偶尔有几辆闪着微弱灯光的载物车从身边经过,轰轰的开向山脚的旅店,微弱的蝉鸣和山里的静谧让我还能听清自己的呼吸声。日出总要早一些,快要六点时,微微的亮开始布满这座沉睡的山。我们不断加快着步子,看着每隔不远就有的用白色大理石修建的宛如英式教堂长廊的石巷。石廊上的漆已经在雨水的冲刷下显得锈迹斑斑,深褐色的砖瓦上铺满了青苔,偶尔还能看见一两个燕子窝搭建在上面。
趁着天亮,我才看清悬崖下的流水,山脚的地势平坦,从山上留下的泉水虽然势力不大,但依旧能清楚的听见它在山谷中的冲撞声。从上往下看去,细细的流水像是一条银白色的长带,在微亮的谷中,还闪着一点点水光。山的对面,尚是翠嫩的新枝斜挂在悬崖上,那些粗壮的根脉一直衍生到山顶,像是网状一般,牢牢地攀附在山面。肥硕的叶子幽绿幽绿的,将新生的枝干掩护起来,悬空的漂浮在空中,微风吹过的时候,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就像是在和山谷打着招呼,向这个刚刚到来的初夏说着悄悄话。
我们乘车到的山顶,雷洞坪到金顶的这一段路程,如果选择乘坐观光缆车上去,也是不错的选择,如果运气好,还可以享受一次腾云驾雾的感觉。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时间还很早,空气中还有微微的雾气,却并不感觉冷。站在一处小斜坡,靠在石栏上向远方望去,山重着山, 隐隐约约的,望不到尽头。云成朵状分布,小块小块的,笼罩着山峰。这些青草都还稚嫩,刚开的雏菊还有偶尔飞过的柳絮,映着不远处的佛塔,母亲裹着头巾从声旁经过,表妹一如既往的拿着相机拍摄,这种安宁的美,一直都寄托着我对山的感恩。
华藏寺上烟雾缭绕,香客来来往往,从阶梯第一层开始揖拜,长长的檀香举在头顶,虔诚的向佛像走去。常青树和柏松栽种在阶梯两旁,用大理石做成的白象,以及刻着铭文的青铜鼎,还有抬头就能望见得金佛。我转身寻找着母亲的身影,她佝偻着身子,将沉香插进鼎中,双手合十,嘴里低低的念叨着,最后深深地一拜,就朝我们的位置走来。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当你虔诚揖拜时,佛就在你的心里。’
当经过大雄宝殿时,正好僧人敲响了铜钟,沉沉的回声,还伴着僧人的吟诵声。我缓缓侧过身,看着这巍峨的建筑物,释迦牟尼佛盘坐着,低垂着眼眉,面相慈和。香烟围绕着整个大殿,蓝天似乎只是做了背景,在这没有任何污染的地方,一切的一切都闲的格外真实。佛语的传唱,没了敦煌的悠远与留恋,却有着峨眉的深沉和安宁。
在山顶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下了山。年轻人总是活跃一点,互相争着走在前面,偶尔停下来取笑着杵着竹竿、颤颤巍巍行走的母亲,在一顿谩骂中,继续嬉笑着往下跑。
山路并不是许多人口中的无趣,当你用心去看时,才会发现它们的美。这些千奇百怪的树干和树枝,在没有人工的栽培下,有的笔直,有的却纵横交错。树枝交叉着树枝,像是武器交锋,扎进了山缝里,青藤将它们缠起来,把阳光分成碎块,洒在黄岩上,蜂鸟和猴儿喜欢停在上面,享受自然给的沐浴。这些绿的植物中偶尔也会点缀着其他颜色的生物,黄的、白的、紫的,木兰的香味淡淡的,当你停留久时,这股幽香就会变得浓郁。山崖下是望不清的薄雾,有游人在下面吆喝着,有时还会传出猴子的啼叫声。大自然最神奇的地方莫过于那些无法想象的奇观,山崖被劈成两半,成六十度对角折叠起来,白云和雾气围绕着这座悬崖,只有树的梢头暴露在人们的视野里。
下午,我们决定朝万年寺的方向前进。从车站出发,一直沿着石路前行,山里独有的流水和蝉鸣声最是安闲,竹子和杨树将古道遮掩起来,新铺的青石路起起伏伏。一名围着薄纱头巾的女人从我们身旁经过,她带着我们去了一家茶房。山里的人总是亲切友好的,她告诉我们,山里的人家有的选择抬滑杆,有的选择开旅店,留下的人就在山里新建的民宿周围栽种茶叶。店家泡了三杯茶给我们,用塑胶纸搭起的篷下摆放着几张木桌和木椅,有几名游人也停在这里歇息。山里的水泡出的茶总是干净透彻的,茶叶竖起飘在水杯里,薄薄的水雾浮在杯口,茶香浸进肺里,驱走了身体里所有的疲惫,就像大山抚摸着我的心脾,带着它感受山泉的洗礼。我们购买了一些茶叶,就又出发前行。
山路弯弯绕绕,才向上翻过几层,又要向下走。母亲在一户人家买了两柱香,或许是因为要向万年寺的方向走,她才少了碎碎念。过了一个小时,有游客告诉我们翻过眼前的阶梯就达到重点了。台阶陡峭且长,一望无尽如同古书里的天梯。两旁的古松柏郁郁葱葱,遮住了初夏的烈阳,清风吹得树叶簌簌的响,使得这段石阶更加的幽深清净。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最后我没有去寺里。看着外面喧嚣的游人,和山顶炉鼎里升起的浓浓的烟雾,靠在石椅上,聆听着寺庙里传出的钟声,山的声音和人的声音合在一起,这些香烟笼罩着这里的一切,将信念和世俗划分开来。
每当日落时分,夕阳留下的最后一缕光,在城里的人看见它们隐没在建筑物的身后;在大漠的人看见它们留在地平面上的一抹红;而在山里的人,在无数次抬头后,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见踪影,如同最熟悉的事物,在恍惚间,忘了去挽留它们的身影。
看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树木,我知道我将回到那个快速的世界,这片悠闲宁静的乐土成了我曾经走过的风景。当那声猿啼尖锐的响起时,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来这座山,来这个留住了我心里最安恬的时光的地方。
山路弯弯绕绕,才向上翻过几层,又要向下走。母亲在一户人家买了两柱香,或许是因为要向万年寺的方向走,她才少了碎碎念。过了一个小时,有游客告诉我们翻过眼前的阶梯就达到重点了。台阶陡峭且长,一望无尽如同古书里的天梯。两旁的古松柏郁郁葱葱,遮住了初夏的烈阳,清风吹得树叶簌簌的响,使得这段石阶更加的幽深清净。不记得走了多长时间,只记得最后我没有去寺里。看着外面喧嚣的游人,和山顶炉鼎里升起的浓浓的烟雾,靠在石椅上,聆听着寺庙里传出的钟声,山的声音和人的声音合在一起,这些香烟笼罩着这里的一切,将信念和世俗划分开来。
每当日落时分,夕阳留下的最后一缕光,在城里的人看见它们隐没在建筑物的身后;在大漠的人看见它们留在地平面上的一抹红;而在山里的人,在无数次抬头后,突然发现它们已经不见踪影,如同最熟悉的事物,在恍惚间,忘了去挽留它们的身影。
看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树木,我知道我将回到那个快速的世界,这片悠闲宁静的乐土成了我曾经走过的风景。当那声猿啼尖锐的响起时,我知道,我还会回来,来这座山,来这个留住了我心里最安恬的时光的地方。
中小学作文网征稿启事
亲爱的朋友:
你好!
还在因为没有一本好的作文书而坐立不安吗
来吧 这里有最时尚的作文欣赏天空
欢迎品鉴
还在为一篇优秀习作无处发表而愁眉苦脸吗
来吧 这里有最便捷的作文刊发平台
期待来稿
大语文时代
阅读与作文水平的高低
将决定你语文素养的优与劣
这里 有写作技法的指导
这里 有作文素材的积累
这里 有同龄孩子的佳作展示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当然
你如果有原创习作需要展示
那么
恭喜你找到了我们
作文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的是反复练笔
请给一次机会
让我们一起见证你的点滴进步
我们不担心你的文字多么稚嫩
我们更不怕你源源不断不断地创作
我手写吾心
只要你的文字有真情实感
我们都会刊发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约吧!
中小学作文网宣言:
红唇两片,笑侃人生;孤笔一支,独抒胸臆。
投稿须知:
1、平台唯一投稿邮箱:280923152@qq.com
2、来稿最好有作者个人简介、照片、作文点评(老师、家长、同学点评都可以)
3、来稿需用word文档编辑,以附件形式发至邮箱。
亲爱的朋友:
你好!
还在因为没有一本好的作文书而坐立不安吗
来吧 这里有最时尚的作文欣赏天空
欢迎品鉴
还在为一篇优秀习作无处发表而愁眉苦脸吗
来吧 这里有最便捷的作文刊发平台
期待来稿
大语文时代
阅读与作文水平的高低
将决定你语文素养的优与劣
这里 有写作技法的指导
这里 有作文素材的积累
这里 有同龄孩子的佳作展示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当然
你如果有原创习作需要展示
那么
恭喜你找到了我们
作文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的是反复练笔
请给一次机会
让我们一起见证你的点滴进步
我们不担心你的文字多么稚嫩
我们更不怕你源源不断不断地创作
我手写吾心
只要你的文字有真情实感
我们都会刊发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约吧!
中小学作文网宣言:
红唇两片,笑侃人生;孤笔一支,独抒胸臆。
投稿须知:
1、平台唯一投稿邮箱:280923152@qq.com
2、来稿最好有作者个人简介、照片、作文点评(老师、家长、同学点评都可以)
3、来稿需用word文档编辑,以附件形式发至邮箱。
今年的冬格外的冷,像是十二月留下它最后的温柔也扬长而去,徒留着这些稀疏的叶子盼着有一天的暖阳,带给这个小城一丝温暖。
我在这个小城市生长了快二十年,记忆中它的变化尤其的大。年幼的时候,街道还是没有围栏的,老人慢悠悠的在大街上行走,因为车少的缘故,没有人催促他们快点前行。那时候的小店铺子一点都不漂亮,黑漆漆的墙壁,两三层玻璃搭起的购物架,有时候从上面拿下一瓶饮料,老板拿在手上拍了拍灰尘,然后递给这几个等待的孩子。过年的时候,城中心还可以放鞭炮,夜里十一点的时候,窗户外面炸响的炮火声围着这个小城,五颜六色的烟花飞到空中,低矮的房屋掩不住这些烟花,小孩子听不清大人的话语,趴在阳台上看着城里的繁华。这些轰轰的声音延续到凌晨三点才渐渐减弱,这时,奶奶会吆喝着三个孩子上床睡觉,那时候,这就是每个城里人最期盼和快乐的一个夜晚。
这个南方的小城从未下过雪,冬天冷极了的时候,偶尔冒出一些雪渣子,还没来得及看清它们的长相,就慢慢融化在手心里。可是,或许是这个小城孩子期盼的声音太过于强烈,那年,生长在这个小城的我们唯一一次看见了大雪。小城的孩子们像是见到了最大的新年礼物,一个个的穿着花花绿绿的袄子,拿着比你自己大一半的深蓝色的桶跑着下楼,即使后面爷爷奶奶的呼声再大,也拦不住这些孩子的好奇。那股唯恐被其他孩子抢先的仗势,拿着一个汤勺大小的铲子,却想要填满整个桶儿的模样,逗的整个院子里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的房屋大都只有两三种颜色,灰黄白,小孩子喜欢在墙上涂鸦,留下自己喜欢的色彩,满是褶皱的水泥墙上,留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红的、蓝的、紫的,即使在时光的冲刷下,那些字迹依旧清晰,像是这个小院舍不得的记忆。城中心是整个小城最热闹的地方,老人拉着孩子到这个地方玩儿,小小的草坪,镂空的大理石围着的小湖,撒下一把面包屑,围过来的一群各种颜色的肥大锦鲤。依靠着树木搭建的茶桌,小孩子跑着互相追逐,老人看着满是人的城市,那个时候还不曾珍惜这些时光。
老人没有贪睡的习惯,清晨到来的时候,摇醒那些还睡的正熟的孩子,慢悠慢悠的去菜市口,小孩子走的摇摇晃晃的,小脑袋也一点一点。菜市场的模样没多大变化,几十个用水泥修砌的台子上面摆满了蔬菜和肉,整个市集里,除了吆喝声和交流声,就只能听见刀子在案板上剁的阵阵回响。偶尔几辆摩托‘嘀嘀’的在这个小巷子里穿来穿去,还有小轿车在人流中被围起时无法前行的焦躁。这个小市集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格外拥挤,随处的摊位将菜市场从里到外占的满满当当,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变得整齐。有时,那些头发花白的太婆太爷会拖着竹篓往建筑物里走,不时的往后望着,看着那些带着蓝帽子的人走远后才笑嘻嘻的把篓子提出来,和买菜的人道歉,称着斤数,没有人舍得去怪罪他们什么,菜市场也不会因此变得不再闹热。
钟鼓楼成了小城人民心中最深的记念物,我不曾知晓在八十年代时,这座大钟是否能记得如同电视里有过的城镇画面,狭窄的街道,满街的三轮车,绿皮的公交,低矮陈旧的建筑物,吵闹的城,随处走动的人群。如今,这里早已变得样子,除了钟楼旁的旧屋子,只有它显得那么有时代感。还是读小学的那年,每天清晨,伴随着七个响彻小城的钟鸣声,还有军人训练时的雄浑声音,一切的一切,随着年长的自己,变得记不清晰。那座大钟,永远的停留在一个时刻,那是全国人民都曾记得的惨痛时间点,可那时的小城人民最舍不得的,就是那再也无法响起的钟鸣。
冬里的风依旧吹得人脸蛋生疼,小城里却有些冷清,似乎是孩子都长大了,曾经‘叽叽喳喳’的小城也在现代化的加速中变得匆忙,唯一留念的红色铺满街道,带来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光,在短暂的时间后变得安静下来。有时候会去感怀一些幼年时的天真和快乐,也开始不希望时间走的越发的快,还会去想象它会不会成长为人们常见的繁华都市。最后却还是希望它就一直这样,有着它一贯的安宁惬意,留着城里老年人独爱的悠闲散漫,即使冬愈发的寒冷,却依然有些随处升起的烟,那是家里的熟悉气息,也是不愿忘记的归属,不愿忘记的小城,不愿忘记的每一个成长的瞬息。
我在这个小城市生长了快二十年,记忆中它的变化尤其的大。年幼的时候,街道还是没有围栏的,老人慢悠悠的在大街上行走,因为车少的缘故,没有人催促他们快点前行。那时候的小店铺子一点都不漂亮,黑漆漆的墙壁,两三层玻璃搭起的购物架,有时候从上面拿下一瓶饮料,老板拿在手上拍了拍灰尘,然后递给这几个等待的孩子。过年的时候,城中心还可以放鞭炮,夜里十一点的时候,窗户外面炸响的炮火声围着这个小城,五颜六色的烟花飞到空中,低矮的房屋掩不住这些烟花,小孩子听不清大人的话语,趴在阳台上看着城里的繁华。这些轰轰的声音延续到凌晨三点才渐渐减弱,这时,奶奶会吆喝着三个孩子上床睡觉,那时候,这就是每个城里人最期盼和快乐的一个夜晚。
这个南方的小城从未下过雪,冬天冷极了的时候,偶尔冒出一些雪渣子,还没来得及看清它们的长相,就慢慢融化在手心里。可是,或许是这个小城孩子期盼的声音太过于强烈,那年,生长在这个小城的我们唯一一次看见了大雪。小城的孩子们像是见到了最大的新年礼物,一个个的穿着花花绿绿的袄子,拿着比你自己大一半的深蓝色的桶跑着下楼,即使后面爷爷奶奶的呼声再大,也拦不住这些孩子的好奇。那股唯恐被其他孩子抢先的仗势,拿着一个汤勺大小的铲子,却想要填满整个桶儿的模样,逗的整个院子里的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候的房屋大都只有两三种颜色,灰黄白,小孩子喜欢在墙上涂鸦,留下自己喜欢的色彩,满是褶皱的水泥墙上,留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名字。红的、蓝的、紫的,即使在时光的冲刷下,那些字迹依旧清晰,像是这个小院舍不得的记忆。城中心是整个小城最热闹的地方,老人拉着孩子到这个地方玩儿,小小的草坪,镂空的大理石围着的小湖,撒下一把面包屑,围过来的一群各种颜色的肥大锦鲤。依靠着树木搭建的茶桌,小孩子跑着互相追逐,老人看着满是人的城市,那个时候还不曾珍惜这些时光。
老人没有贪睡的习惯,清晨到来的时候,摇醒那些还睡的正熟的孩子,慢悠慢悠的去菜市口,小孩子走的摇摇晃晃的,小脑袋也一点一点。菜市场的模样没多大变化,几十个用水泥修砌的台子上面摆满了蔬菜和肉,整个市集里,除了吆喝声和交流声,就只能听见刀子在案板上剁的阵阵回响。偶尔几辆摩托‘嘀嘀’的在这个小巷子里穿来穿去,还有小轿车在人流中被围起时无法前行的焦躁。这个小市集在我幼时的记忆中格外拥挤,随处的摊位将菜市场从里到外占的满满当当,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变得整齐。有时,那些头发花白的太婆太爷会拖着竹篓往建筑物里走,不时的往后望着,看着那些带着蓝帽子的人走远后才笑嘻嘻的把篓子提出来,和买菜的人道歉,称着斤数,没有人舍得去怪罪他们什么,菜市场也不会因此变得不再闹热。
钟鼓楼成了小城人民心中最深的记念物,我不曾知晓在八十年代时,这座大钟是否能记得如同电视里有过的城镇画面,狭窄的街道,满街的三轮车,绿皮的公交,低矮陈旧的建筑物,吵闹的城,随处走动的人群。如今,这里早已变得样子,除了钟楼旁的旧屋子,只有它显得那么有时代感。还是读小学的那年,每天清晨,伴随着七个响彻小城的钟鸣声,还有军人训练时的雄浑声音,一切的一切,随着年长的自己,变得记不清晰。那座大钟,永远的停留在一个时刻,那是全国人民都曾记得的惨痛时间点,可那时的小城人民最舍不得的,就是那再也无法响起的钟鸣。
冬里的风依旧吹得人脸蛋生疼,小城里却有些冷清,似乎是孩子都长大了,曾经‘叽叽喳喳’的小城也在现代化的加速中变得匆忙,唯一留念的红色铺满街道,带来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光,在短暂的时间后变得安静下来。有时候会去感怀一些幼年时的天真和快乐,也开始不希望时间走的越发的快,还会去想象它会不会成长为人们常见的繁华都市。最后却还是希望它就一直这样,有着它一贯的安宁惬意,留着城里老年人独爱的悠闲散漫,即使冬愈发的寒冷,却依然有些随处升起的烟,那是家里的熟悉气息,也是不愿忘记的归属,不愿忘记的小城,不愿忘记的每一个成长的瞬息。
百度小说人气榜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拜登确诊恶性前列腺癌2744610
- 2XLG选手YOU被曝辱华假赛2337661
- 3雷霆抢七淘汰掘金2179520
- 4Spirit夺PGL阿斯塔纳2025冠军1968381
- 5阿森纳1-0纽卡锁定欧冠资格1386684
- 6莎头世乒赛混双首战告捷1234850
- 7百度黄山音乐节开唱即巅峰1208616
- 8TES 2:1战胜TT884672
- 9曼城0-1送水晶宫队史首冠704682
- 10TTG创造奇迹拿下ACL冠军453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