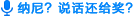1.
我和安喜有气无力的躺在一个不知名村口的干粪堆里取暖。粪堆外大雪纷飞。
‘大富我饿...’
安喜和我上次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还是夏天。其实我也饿的特别难受,对他鼓励让他坚持下去的话都没力气说出口了。只是抬手指了一下头顶的干粪对他说吃。
‘大富你说屎壳郎天天吃屎也能活,这屎是不是也能吃。’
我明白这是在胃酸快要消化胃的时候安喜已经打定主意要吃屎充饥了。它只不过让我随便说句话坚定他的勇气。
‘能’,我艰难的翻了个身。我实在不愿意亲眼看到发小吃屎的样子。
‘这个是牛粪吧,竟然有我们老家沟子里木耳的香气。’
‘咦?这个羊粪蛋咋酸酸甜甜的,一股咱村李寡妇奶头的草莓味。’
安喜的吞咽声打断了我回忆木耳和草莓的味道。我咽了咽口水,说了声牛逼,沉沉睡去。
’
我和安喜有气无力的躺在一个不知名村口的干粪堆里取暖。粪堆外大雪纷飞。
‘大富我饿...’
安喜和我上次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还是夏天。其实我也饿的特别难受,对他鼓励让他坚持下去的话都没力气说出口了。只是抬手指了一下头顶的干粪对他说吃。
‘大富你说屎壳郎天天吃屎也能活,这屎是不是也能吃。’
我明白这是在胃酸快要消化胃的时候安喜已经打定主意要吃屎充饥了。它只不过让我随便说句话坚定他的勇气。
‘能’,我艰难的翻了个身。我实在不愿意亲眼看到发小吃屎的样子。
‘这个是牛粪吧,竟然有我们老家沟子里木耳的香气。’
‘咦?这个羊粪蛋咋酸酸甜甜的,一股咱村李寡妇奶头的草莓味。’
安喜的吞咽声打断了我回忆木耳和草莓的味道。我咽了咽口水,说了声牛逼,沉沉睡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