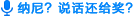何夕在草叶间醒来时旭日照脸,她下意识地用手挡了一下;视觉的错觉中太阳落在她掌中,恍惚她还记得他举杯微笑的温柔和熙。梦中——何夕不确定是不是梦,她转一下身,撒嘴轻笑,其实谁又知道这世界不是谁的梦境所造?窗外有一蝶飞舞而过,蝶影有一瞬间映入她的瞳孔里,无端变化莫测……
何夕依稀记得护龙河边他打马而过的身影,那是三月初春的时节,两岸柳色新绿,和风暖熙。他轻骑简从,踏春而来,春风抚面,谈笑间一池风华溶溶;她从道旁草木丛中无意间抬了一下头只那一瞥她便看痴了心生万种风情遂化了一阵风随他而去,她让他如水藻般的鬓发亲吻她的脸庞。从此有他在的那紫陌红尘中独得了春风十里……
何夕。何夕……他说今夕何夕得此殊丽?何夕是在月华满城中降临的,春夜的微风习习醉人,风中开满了如雪的梨花,在他的庭前院中满天洒落,她施施然从梨花深处走向他。笑容晏晏,巧俏盼兮,她说“见君倾情,为君而来。”他呆立阶前半响不语,随即豁然一笑,牵过她的手同赏满天梨花雨。
那年,他17岁,刚出任贵州防御使,正是玉树正好时。他从不问何夕是何人,只是与她相守情好,相恋亦相惜。史册上何夕姓王,他说‘何’字凄惶不可以姓之,便随手拟了一‘王’字。从此她成了他的秦国夫人王氏……彼时满天飞雪,窗外瘦梅凌雪绽了数点红霞,暖阁中琼炉香暖,那提了‘王’字的玉板笺却被一阵风雪扫落,劲风强雪突袭而来吹打窗扉支格轰响,顿时香消暖退渺不可追。未及等人重闭门窗便一声丧钟扶摇而来,未及己有人来报圣上薨世,那一刻,他呆若木鸡仿佛完然没听清奏报内容……“怎么会?昨夜他还和我谈笑如常,出去时他还和皇叔弈局正酣……”他怔怔然自语跌坐椅上:“皇叔…?皇叔…?”银雪红梅映在他眸中全成了灰色魅影。不久后太宗及位,烛影斧声之谈广传天下禁而不灭。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他饮醉琼浆时时常兴起而歌这两曲哀辞,《薤露歌》、《蒿里》皆是丧歌,何夕想起长久的岁月中匍匐在田间陌上之时时常听到寻常百姓家的送葬队伍吹拉吟唱这两支曲,那时漫天扯絮一样飘着白纸钱,那歌声夹着哭声听来是骤雨夜的哀风呼号。他时常唱着唱着就踏歌起舞,明媚的笑容中刻着泪痕,眼眸深邃吞了日月……他说“何夕,何夕我命不久矣了……”说着他轻轻靠进何夕的肩窝里,散开的长发如一块披帛从她肩头垂落。那年他二十二岁被叔父加封为检校太尉,世人眼中他是皇室贵胄、圣皇遗子,是名传后世的贤王;实则他不过是一介囚徒……
何夕没有想到他的生命还有一年,他在二十三岁时突然长逝;从此玉树凋敞,棠棣失华,春不再临——紫陌红尘皆为飞灰。她还记得那年也是三月春日,他奉招入宫,回来时多了一壶赐酒。那时他四岁的长子己被接到宫中两年有余了,那日的春夜依旧芳菲满城,他牵了何夕的手说“你我尘缘尽矣,今夜你再为我舞一场梨花雨吧?”他欣赏满天梨花琼絮,自斟自饮,一壶饮尽他贺然倒进琼琳碎玉中被埋葬,她最后只记得他举杯微笑的一如那年初见他的模样……她就此盾消灭迹飘然远去,归于田间陌上、幽山密林闲看千载光阴如梭,偶尔想想那年那人……
何夕依稀记得护龙河边他打马而过的身影,那是三月初春的时节,两岸柳色新绿,和风暖熙。他轻骑简从,踏春而来,春风抚面,谈笑间一池风华溶溶;她从道旁草木丛中无意间抬了一下头只那一瞥她便看痴了心生万种风情遂化了一阵风随他而去,她让他如水藻般的鬓发亲吻她的脸庞。从此有他在的那紫陌红尘中独得了春风十里……
何夕。何夕……他说今夕何夕得此殊丽?何夕是在月华满城中降临的,春夜的微风习习醉人,风中开满了如雪的梨花,在他的庭前院中满天洒落,她施施然从梨花深处走向他。笑容晏晏,巧俏盼兮,她说“见君倾情,为君而来。”他呆立阶前半响不语,随即豁然一笑,牵过她的手同赏满天梨花雨。
那年,他17岁,刚出任贵州防御使,正是玉树正好时。他从不问何夕是何人,只是与她相守情好,相恋亦相惜。史册上何夕姓王,他说‘何’字凄惶不可以姓之,便随手拟了一‘王’字。从此她成了他的秦国夫人王氏……彼时满天飞雪,窗外瘦梅凌雪绽了数点红霞,暖阁中琼炉香暖,那提了‘王’字的玉板笺却被一阵风雪扫落,劲风强雪突袭而来吹打窗扉支格轰响,顿时香消暖退渺不可追。未及等人重闭门窗便一声丧钟扶摇而来,未及己有人来报圣上薨世,那一刻,他呆若木鸡仿佛完然没听清奏报内容……“怎么会?昨夜他还和我谈笑如常,出去时他还和皇叔弈局正酣……”他怔怔然自语跌坐椅上:“皇叔…?皇叔…?”银雪红梅映在他眸中全成了灰色魅影。不久后太宗及位,烛影斧声之谈广传天下禁而不灭。
薤上露,何易晞。
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他饮醉琼浆时时常兴起而歌这两曲哀辞,《薤露歌》、《蒿里》皆是丧歌,何夕想起长久的岁月中匍匐在田间陌上之时时常听到寻常百姓家的送葬队伍吹拉吟唱这两支曲,那时漫天扯絮一样飘着白纸钱,那歌声夹着哭声听来是骤雨夜的哀风呼号。他时常唱着唱着就踏歌起舞,明媚的笑容中刻着泪痕,眼眸深邃吞了日月……他说“何夕,何夕我命不久矣了……”说着他轻轻靠进何夕的肩窝里,散开的长发如一块披帛从她肩头垂落。那年他二十二岁被叔父加封为检校太尉,世人眼中他是皇室贵胄、圣皇遗子,是名传后世的贤王;实则他不过是一介囚徒……
何夕没有想到他的生命还有一年,他在二十三岁时突然长逝;从此玉树凋敞,棠棣失华,春不再临——紫陌红尘皆为飞灰。她还记得那年也是三月春日,他奉招入宫,回来时多了一壶赐酒。那时他四岁的长子己被接到宫中两年有余了,那日的春夜依旧芳菲满城,他牵了何夕的手说“你我尘缘尽矣,今夜你再为我舞一场梨花雨吧?”他欣赏满天梨花琼絮,自斟自饮,一壶饮尽他贺然倒进琼琳碎玉中被埋葬,她最后只记得他举杯微笑的一如那年初见他的模样……她就此盾消灭迹飘然远去,归于田间陌上、幽山密林闲看千载光阴如梭,偶尔想想那年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