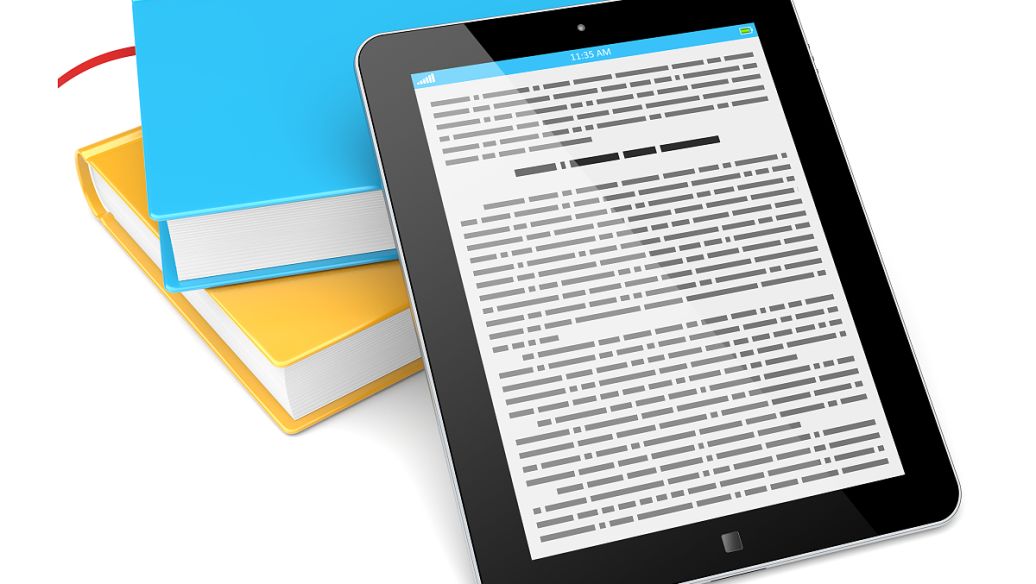贾雨村的出身是诗书一脉,但是没享福,孤零,穷,出场的时候,虽然形态雄壮、才情傲人,志气高昂,但要卖字为生,情形是很糟的。
不过看起来运气不坏,遇到甄士隐的接济,又遇到“侥幸”的青眼,脱运交运,中进士,一下子平步青云。
到这里,贾雨村基本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形象,虽然前脚拿了钱,隔天就走,连招呼也不打,显得有点急色;刚发达了,就去讨个恩人的丫鬟当妾,稍微有点下作。
但也还不算大事,穷人乍富,翻身农奴把歌唱,吃相不免有点难看。至于娇杏,他大概也是戏文看多了,虽然对方不是后花园赠金的“小姐”,但好歹也是个慧眼如炬的大姐,他急于搞一出大登科以后的小登科,可以理解。
但文风突然变了,他居然被革职了:
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这一段是“文眼”,值得细品。
书中所写,贾雨村的倒霉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贪酷之弊”,一个是“恃才侮上”。
先看“贪”。
“贪”者,自然是图财。雨村一个穷书生,好不容易当了知府,而且干了快一年。俗语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然,民间传说例有夸张,不能全当真,但也不会全脱根基,可见只要当到这个级别的官,即便不是“贪酷”,想来也可迅速致富。
但看看贾雨村:
雨村罢官之后,“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甲戌侧批:先云“根基已尽”,故今用此四字,细甚!]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看起来很潇洒,到处游山玩水,但一个堂堂进士,前任知府,到了扬州,却不逛了。
雨村正值偶感风寒,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方渐愈。一因身体劳倦,二因盘费不继,也正欲寻个合式之处,暂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闻得盐政欲聘一西宾,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
竟然落到要去谋求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了。
在古代,教私塾这个事情,当然也谈不上有啥不好,但肯定也不算啥好的工作,所以,差不多是秀才或者老童生的专属,连举人都绝不肯屈就的,雨村居然想去干这个,还托人去谋求。
这成何体统?他又哪里像个有钱人?
没有钱,困窘,身边还有朋友,就算汇兑不利,却不去借,可见至少没啥大钱,这么看,“贪”自然就不太容易站住。
那“酷”又如何?
这是必然有的。
一个人当地方官,自然要做事,要完成KPI。地方上公务繁杂,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项硬指标,一是刑名,二是钱粮。
“刑名”就是司法,这是维持地方稳定的主要手段,也反应了政府本身的口碑,历代地方官风纪考评,刑名必是第一;
“钱粮”就是税收,这是国计民生,更是不可差池,官声再好,销售指标没完成,肯定不行。
当官的要想管理地方,这些事总不能靠自己干,是要依托下属去做的,而做这些事的人,就是地方上的“吏”。
地方上的“吏”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房书办,所谓“各房”,和朝廷的设置一致,朝廷有“刑部”,地方上也有“刑房”,书办的工作职能,和朝廷的尚书也差不多,属于地方上的专业行政人员。
《水浒传》里的宋江,职位叫“押司”,其实就是“吏”,书中没有明说,但估计就是“刑房书办”,看看县官对他的态度,那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多么的殷切照顾。
为什么?因为官是有任期的,经常变的,而且朝廷规定,本地人不许在本地当官。但是,官经常换,吏却是不换的,而且都是本地人,他们掌握了地方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信息,长期把持地方,其中几个书办的职位,实际上还是世袭的——比如“户房书办”,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本“鱼鳞册”,只有他们才知道具体的田亩数字,纳税多少,外人概莫能知,所以慢慢就演变为是父死子袭的状态了。
可见,“吏”虽然被称为小吏,社会地位不高,名义上甚至属于贱民,有子孙不可参加科举等限制,但却是地头蛇,是地方上真正的行政主持,是每一个官员完成指标的执行者,从某种角度说,是他们掌握着官员的前程。
所以,新官到任,如何和“吏”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如果当官的手段不够,本身财力不足,就会被他们辖制,反过来,当官的手段高明,或者来头极大,则能管控住他们。当然,大部分情况,其实是各取所需,各管一摊,有合作,也有斗争,大致是因袭前状,相安无事。
以贾雨村一介寒士的背景和财力,让他去买通这些人,应该做不到;而以他性格中的狂妄,让他低声下气去结交这些人,可能性好像也不大;但雨村人是极聪明极有抱负的,也是急切地想出成绩的,既要完成任务,就必须让底下的人干活。
脂批说雨村有“奸雄本色”,比之操莽,那大概也只有软硬两手:
所谓软,就是承诺好处,让底下人去发财,如果可能的话,顺便自己也捞点;所谓硬,则是搞承包、压指标,限期完成。
简而言之,给不了钱,那就给政策。
这样给政策,应该就是“暗结虎狼之属”的由来了,而他本人的“酷”的官声,是一定跑不了的,但是客观的说,除了这招,又能有啥其他办法呢?而且,这句话放到现代,大致也就是个“管理不利”、“工作作风极端粗暴”的意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所以说,贾雨村这种程度的“贪酷”,其实是常态,为了按时高效完成工作,甚至是不得不如此,上司以此为由头弹劾,不是不可以,但放在官场这个大环境看,未免小题大做了。
那贾雨村到底怎么被开革了呢?而且居然这么快?
我们再回头细看弹劾的文本:
“生情狡猾,擅纂礼仪”——这句是说他不合礼教,属于大帽子,忽略。
下两句是重点——“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
“沽清正之名”,是说他表现得很像个清官,而且是“沽”,说明他很看重这一点,形象工程做的很好;
“暗结虎狼之属”,是说他自己不出面,靠下属去做坏事,
于是有了“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结论。
“暗结虎狼之属”是上纲上线,那么这个“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结论又如何?
这也是胡扯,甚至就是随口说的。
因为从处理结果上看,上司的考语这么重,乃至“龙颜大怒”,贾雨村也只是被免官,没有追究其他责任。
是上司想轻放他?不可能,否则何必参他,而且已经“上达天听”,真有证据,别说本意未必想轻纵,客观上也已经无法轻纵了。
“贪酷”和“暗结虎狼之属”都不重要,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显然,是“恃才侮上”和 “沽清正之名”。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贾雨村在第一次当官的时候,不是“沽清正之名”,在当时的环境来说,他其实就是个清官。
因为是清官,他才有道德荣誉感,有工作责任感,事实上,以他的才干,本职应该做的不错,甚至很出色,故此,他才具备了“恃才侮上”的合法性。而这正是他把上下都得罪光了的原因,也是上司要“寻了个空隙”才能参他的原因,才是他被免职的“该部文书一到,本府官员无不喜悦”的真正原因。
真要是派系斗争纵横排阖的“暗结虎狼之属”,这些官员总有几个是他“暗结”才对,“无不喜悦”?岂有此理嘛。
革职令到时,他“心中虽十分惭恨”,但这里的“惭”由何出?“恨”由何生?
他“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时,到底想到了什么?
这些,我们读者自然不知道,但我们看到,等他再次发达以后,他弃恩人亲女于不顾,他为几把扇子逼死人命。
人一直落魄,倒也没什么,眼不见心不烦,不管他人坐在宝马里哭,还是坐在自行车上笑,横竖都和自己无关,他一个穷鬼,宝马固然没有,自行车也是没有的,没啥好比的。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第二次落魄,他是生生的从坐宝马的,掉到了骑自行车的,境况当然是比当初要好一点,但心态恐怕到是加倍低落了。
贾雨村是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的,他发现,草根出身的自己,所谓的理想、抱负,都是可笑的。当贪官,至少还能结交上司,交好同事,当清官,却只能落到革职的境地。所以,他发现自己其实是没有资格当清官的,也是不配当清官的,更何况,他也绝不会愿意自己再一次去过穷苦的日子。这就是他脱胎换骨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把“护官符”看得高于一切的原因。靠着这点悟性,他终于变成了“兴隆街大爷”,虽然他最后还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了,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才是假语村言,这才是《石头记》通部最大的狡猾之笔,读者诸君若不细读,真是要被作者瞒过的。
(和几个同好一起搞了个微信公众号,叫“红楼梦研究”:hlmyl001 ,私人号,主要是推红楼梦的每回精读,也搞了个音频http://www.lizhi.fm/1410560/2519578095014823942,欢迎红迷来访)
不过看起来运气不坏,遇到甄士隐的接济,又遇到“侥幸”的青眼,脱运交运,中进士,一下子平步青云。
到这里,贾雨村基本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人物形象,虽然前脚拿了钱,隔天就走,连招呼也不打,显得有点急色;刚发达了,就去讨个恩人的丫鬟当妾,稍微有点下作。
但也还不算大事,穷人乍富,翻身农奴把歌唱,吃相不免有点难看。至于娇杏,他大概也是戏文看多了,虽然对方不是后花园赠金的“小姐”,但好歹也是个慧眼如炬的大姐,他急于搞一出大登科以后的小登科,可以理解。
但文风突然变了,他居然被革职了:
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
这一段是“文眼”,值得细品。
书中所写,贾雨村的倒霉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有些贪酷之弊”,一个是“恃才侮上”。
先看“贪”。
“贪”者,自然是图财。雨村一个穷书生,好不容易当了知府,而且干了快一年。俗语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然,民间传说例有夸张,不能全当真,但也不会全脱根基,可见只要当到这个级别的官,即便不是“贪酷”,想来也可迅速致富。
但看看贾雨村:
雨村罢官之后,“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协,[甲戌侧批:先云“根基已尽”,故今用此四字,细甚!]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
看起来很潇洒,到处游山玩水,但一个堂堂进士,前任知府,到了扬州,却不逛了。
雨村正值偶感风寒,病在旅店,将一月光景方渐愈。一因身体劳倦,二因盘费不继,也正欲寻个合式之处,暂且歇下。幸有两个旧友,亦在此境居住,因闻得盐政欲聘一西宾,雨村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且作安身之计。
竟然落到要去谋求个家庭教师的职位了。
在古代,教私塾这个事情,当然也谈不上有啥不好,但肯定也不算啥好的工作,所以,差不多是秀才或者老童生的专属,连举人都绝不肯屈就的,雨村居然想去干这个,还托人去谋求。
这成何体统?他又哪里像个有钱人?
没有钱,困窘,身边还有朋友,就算汇兑不利,却不去借,可见至少没啥大钱,这么看,“贪”自然就不太容易站住。
那“酷”又如何?
这是必然有的。
一个人当地方官,自然要做事,要完成KPI。地方上公务繁杂,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项硬指标,一是刑名,二是钱粮。
“刑名”就是司法,这是维持地方稳定的主要手段,也反应了政府本身的口碑,历代地方官风纪考评,刑名必是第一;
“钱粮”就是税收,这是国计民生,更是不可差池,官声再好,销售指标没完成,肯定不行。
当官的要想管理地方,这些事总不能靠自己干,是要依托下属去做的,而做这些事的人,就是地方上的“吏”。
地方上的“吏”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房书办,所谓“各房”,和朝廷的设置一致,朝廷有“刑部”,地方上也有“刑房”,书办的工作职能,和朝廷的尚书也差不多,属于地方上的专业行政人员。
《水浒传》里的宋江,职位叫“押司”,其实就是“吏”,书中没有明说,但估计就是“刑房书办”,看看县官对他的态度,那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多么的殷切照顾。
为什么?因为官是有任期的,经常变的,而且朝廷规定,本地人不许在本地当官。但是,官经常换,吏却是不换的,而且都是本地人,他们掌握了地方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信息,长期把持地方,其中几个书办的职位,实际上还是世袭的——比如“户房书办”,因为他们手里有一本“鱼鳞册”,只有他们才知道具体的田亩数字,纳税多少,外人概莫能知,所以慢慢就演变为是父死子袭的状态了。
可见,“吏”虽然被称为小吏,社会地位不高,名义上甚至属于贱民,有子孙不可参加科举等限制,但却是地头蛇,是地方上真正的行政主持,是每一个官员完成指标的执行者,从某种角度说,是他们掌握着官员的前程。
所以,新官到任,如何和“吏”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如果当官的手段不够,本身财力不足,就会被他们辖制,反过来,当官的手段高明,或者来头极大,则能管控住他们。当然,大部分情况,其实是各取所需,各管一摊,有合作,也有斗争,大致是因袭前状,相安无事。
以贾雨村一介寒士的背景和财力,让他去买通这些人,应该做不到;而以他性格中的狂妄,让他低声下气去结交这些人,可能性好像也不大;但雨村人是极聪明极有抱负的,也是急切地想出成绩的,既要完成任务,就必须让底下的人干活。
脂批说雨村有“奸雄本色”,比之操莽,那大概也只有软硬两手:
所谓软,就是承诺好处,让底下人去发财,如果可能的话,顺便自己也捞点;所谓硬,则是搞承包、压指标,限期完成。
简而言之,给不了钱,那就给政策。
这样给政策,应该就是“暗结虎狼之属”的由来了,而他本人的“酷”的官声,是一定跑不了的,但是客观的说,除了这招,又能有啥其他办法呢?而且,这句话放到现代,大致也就是个“管理不利”、“工作作风极端粗暴”的意思,也算不上什么大事。
所以说,贾雨村这种程度的“贪酷”,其实是常态,为了按时高效完成工作,甚至是不得不如此,上司以此为由头弹劾,不是不可以,但放在官场这个大环境看,未免小题大做了。
那贾雨村到底怎么被开革了呢?而且居然这么快?
我们再回头细看弹劾的文本:
“生情狡猾,擅纂礼仪”——这句是说他不合礼教,属于大帽子,忽略。
下两句是重点——“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
“沽清正之名”,是说他表现得很像个清官,而且是“沽”,说明他很看重这一点,形象工程做的很好;
“暗结虎狼之属”,是说他自己不出面,靠下属去做坏事,
于是有了“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结论。
“暗结虎狼之属”是上纲上线,那么这个“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的结论又如何?
这也是胡扯,甚至就是随口说的。
因为从处理结果上看,上司的考语这么重,乃至“龙颜大怒”,贾雨村也只是被免官,没有追究其他责任。
是上司想轻放他?不可能,否则何必参他,而且已经“上达天听”,真有证据,别说本意未必想轻纵,客观上也已经无法轻纵了。
“贪酷”和“暗结虎狼之属”都不重要,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呢?
显然,是“恃才侮上”和 “沽清正之名”。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贾雨村在第一次当官的时候,不是“沽清正之名”,在当时的环境来说,他其实就是个清官。
因为是清官,他才有道德荣誉感,有工作责任感,事实上,以他的才干,本职应该做的不错,甚至很出色,故此,他才具备了“恃才侮上”的合法性。而这正是他把上下都得罪光了的原因,也是上司要“寻了个空隙”才能参他的原因,才是他被免职的“该部文书一到,本府官员无不喜悦”的真正原因。
真要是派系斗争纵横排阖的“暗结虎狼之属”,这些官员总有几个是他“暗结”才对,“无不喜悦”?岂有此理嘛。
革职令到时,他“心中虽十分惭恨”,但这里的“惭”由何出?“恨”由何生?
他“面上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时,到底想到了什么?
这些,我们读者自然不知道,但我们看到,等他再次发达以后,他弃恩人亲女于不顾,他为几把扇子逼死人命。
人一直落魄,倒也没什么,眼不见心不烦,不管他人坐在宝马里哭,还是坐在自行车上笑,横竖都和自己无关,他一个穷鬼,宝马固然没有,自行车也是没有的,没啥好比的。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第二次落魄,他是生生的从坐宝马的,掉到了骑自行车的,境况当然是比当初要好一点,但心态恐怕到是加倍低落了。
贾雨村是吸取了这次深刻教训的,他发现,草根出身的自己,所谓的理想、抱负,都是可笑的。当贪官,至少还能结交上司,交好同事,当清官,却只能落到革职的境地。所以,他发现自己其实是没有资格当清官的,也是不配当清官的,更何况,他也绝不会愿意自己再一次去过穷苦的日子。这就是他脱胎换骨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把“护官符”看得高于一切的原因。靠着这点悟性,他终于变成了“兴隆街大爷”,虽然他最后还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了,但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才是假语村言,这才是《石头记》通部最大的狡猾之笔,读者诸君若不细读,真是要被作者瞒过的。
(和几个同好一起搞了个微信公众号,叫“红楼梦研究”:hlmyl001 ,私人号,主要是推红楼梦的每回精读,也搞了个音频http://www.lizhi.fm/1410560/2519578095014823942,欢迎红迷来访)